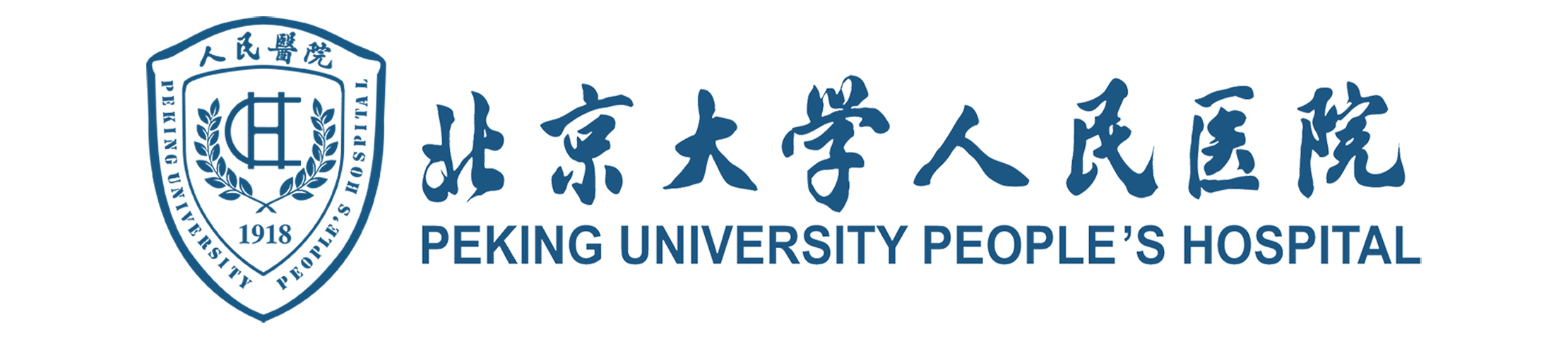向生命致敬 树医者典范
2021年12月8日下午,由环球时报、生命时报主办的2021 “敬佑生命·荣耀医者”第六届公益评选颁奖活动在北京人民日报社举行。
会上,揭晓了 “2021荣耀医者榜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将六项大奖收入囊中,一个团队和五位专家榜上有名——

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美德,生命时报社自2016年发起首届“敬佑生命•荣耀医者”公益活动,活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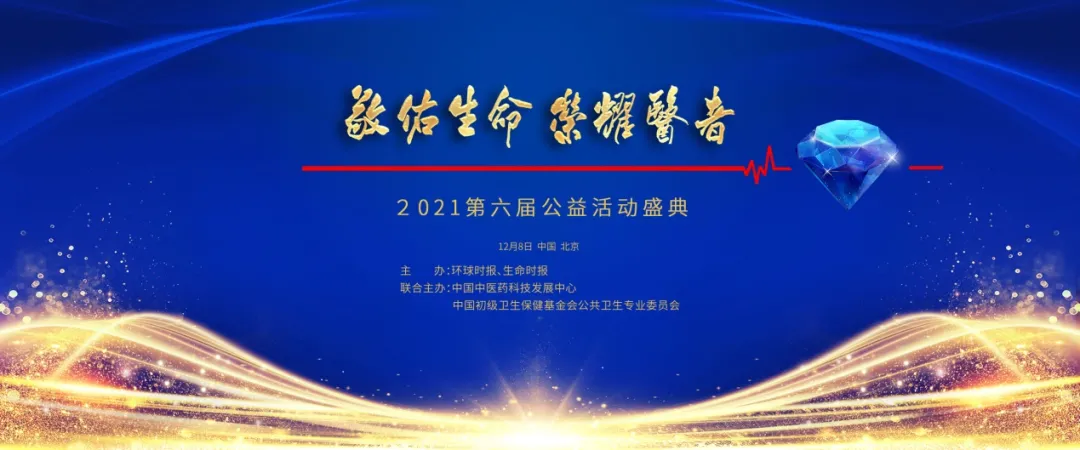
今年,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85家医院411位医务人员、51个诊疗团队提交的报名材料。最终,经过21位院士、国医大师,38位院领导,23位主委及权威专家,5位主流媒体负责人的评审和讨论,公平公正地选出了今年111位荣耀医者及团队。
会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嘉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等出席公益活动并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海霞主持本次活动。
医者致敬
他们点赞

胸外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创建于1952年,以胸腔镜胸部微创手术及肺癌微创综合外科治疗为主要特色。科室近年先后被评为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北京市肺癌规范化诊疗示范中心、中国医师协会胸腔镜医师培训学院、北京大学模范职工小家等,是国内外公认的我国胸腔镜胸部微创手术技术力量最为雄厚的“排头兵”单位。
胸外科:提供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医疗
临床工作需要的是扎实的医学知识、清晰的临床思维和精良的手术技术,需要的是对病人身体的疗护和心理的抚慰。前者是高度,后者是温度。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医疗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每一位“胸科人”一贯的努力方向。
在国内,提到胸腔镜手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王俊院士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这里曾经开创了中国胸腔镜领域的众多“第一”——领导制定了胸腔镜手术的国家规范,创立了肺癌微创手术的“王氏技术”,并写入英文专著和《柳叶刀 肿瘤》杂志的封面文章;主导的肺癌微创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和推广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我国肺癌诊疗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全体胸科人勤奋敬业、团结协作、勇于担当是分不开的。
一以贯之的勤奋和努力。科室坚持了15年的制度——周四大查房制度,让胸外科领域的诸多创新在这里不断开花结果。每周四,科室全体人员都会在早晨六点半上班,大家会一起讨论制定疑难重症病例的诊疗方案,总结分析既往病例的诊治得失,学习诊疗新进展,探讨科研新思路。多年来,这个制度从未中断。
团结一致,精诚合作。胸外科的成员们既有在临床工作上的相互补缺和相互帮衬,又有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上的相互启发和相互成就。王俊院士鼓励,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特长,对其他同事要以诚相待,精诚合作,这样不仅能为科室创造友善团结的氛围,还能创造自由的竞争环境,让年轻人朝气蓬勃、信心十足,拥有充分的上升空间。
桃李天下,春晖四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是北京大学医学部胸心外科博士点、博士后工作站、胸外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胸心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胸外科组组长单位。截至目前,科室累计培养研究生120余名;牵头制定全国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及专科医师培训标准;主编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创立中国胸腔镜手术培训模式,培训了我国早期80%以上的胸腔镜外科医生。目前活跃在国内胸外科领域的许多骨干人才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服务社会,勇于担当。优秀的团队来源于社会,也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作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国家级医疗技术团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时刻坚守着服务社会的使命担当。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战斗中,在2010年青海玉树的地震灾区,在屡次应急救援的国家医疗队中,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在支援西藏、支援新疆、支援云南的国家医疗援助任务中,北大人民医院胸外科从未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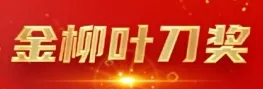
耳鼻喉科 余力生

余力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常委,国际耳内科学会中国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耳科学杂志》副主编,《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编委,德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会员;获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余力生:让数千聋儿重获“新声”
在职业生涯救治的无数个患者中,有1例病例始终让余力生印象深刻。一次在云南做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后,当地医院请他看了一个14岁的患儿,高烧一月不止,伴发严重头疼,持续抗生素治疗无效。在接诊时余力生根据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很快判定患儿是胆酯瘤同时伴有脑脓肿。这个家庭非常特殊,3个孩子已经有两个去世,这个患儿是家中的唯一希望。当地医生提出能否转到北京治疗,余力生敏锐判断出转运途中患儿很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决定退掉机票,当日急诊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最终半个小时放出了脑子里50毫升的脓液,使患儿转危为安,当晚体温就恢复正常。余力生心中很清楚,这次冒了极大的风险,如果脑子的脓液放得太快,很容易发生脑疝。但余力生更明白,作为医生他不接这活儿,患儿肯定死亡,冒险是最好的选择。
出手术室后,患儿母亲拿着一个层层包裹的小包,里面都是零碎钱。因家贫,孩子母亲拿出家里所有的钱表示感谢。余力生拒绝了这份“好意”。给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余力生在专业领域的渊博学识和精湛技术,更打动人的是他的医者仁心。他常说:“要做有技术的医生,更要做有温度的医生,温度在于对患者的温和耐心、认真负责,也在于医者胸怀的博大和博爱。”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承担了多项贫困聋儿救治项目,数千名聋儿通过植入人工耳蜗重获“新声”,减轻了他们的家庭负担,更使他们能正常地融入学校和社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多年来积极响应中组部组织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作为科主任的余力生更是亲力亲为、冲锋在前。2016年8月,应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邀请,余力生来到雪域高原,刚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来到手术室。一位幼小的藏族女孩,多年的中耳炎导致右耳听力下降,等待着余力生亲自主刀手术。更衣、刷手、铺台、消毒……在自身血氧饱和度只有80%~85%的情况下,余力生一边手术,一边给当地的医生们讲解。在耳科显微镜前他目光如炬,提捻柳叶刀的动作自信娴熟,浑然不觉自己身处海拔3600米的高原。术中彻底清除患儿中耳内的胆固醇肉芽肿,安装人工听骨,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结束摘下口罩的瞬间,他的口唇是青紫的,在吸氧稍事休息后,又开始了下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了让更多藏族同胞的孩子能早日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在短短两天半时间内他就完成了11例人工耳蜗植入,接近既往援藏1年的人工耳蜗手术量。
在30年的行医生涯中,余力生始终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前人,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国际第一。余力生是最早在国内将软骨技术引入中耳手术,并对这一手术技术进行了推广;完成了我国大陆首例双侧人工耳蜗植入;完成了我国首例单侧聋患者人工耳蜗植入、首例梅尼埃病患者人工耳蜗植入等;提出了糖皮质激素耳后局部给药这一国际首创的治疗方式,同时提出梅尼埃病新的发病机制,并将手术方式进行了优化改良,新术式不会扰动中、内耳结构,风险小,疗效进一步得到改进。
作为耳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余力生知道自己有责任让先进的技术推广到全国更多地方,尤其是提升基层诊疗技术水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每年举办耳科诊断与治疗进展学习班,指导全国数十家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余力生则毫无保留地与全国各地的同道交流,倾囊相授临床诊疗中新的心得和体会。科室的进修医生从远疆到近郊,无数青年医者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其中不少医生已成长为当地的知名专家,独当一面。
在余力生看来,医生是一个积德的行业,医者仁心是践行一生的诺言。用大仁大爱给冰冷的柳叶刀赋予炽热的温度,会让更多人的世界动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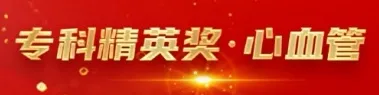
心内科 陈红

陈红,心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急性心肌梗死早期预警和干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副主任。
陈红:医者是与生命在对话
在患者眼里,她是充满同理心、和蔼可亲、医术高超的陈大夫;在学生眼中,她是严格要求、追求完美、亦师亦友的陈老师。她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陈红教授。
作为科室的当家人,陈红始终坚守医者仁心、传承医者仁术,自始至终追求着不曾改变的医者理想。心血管系统疾病往往起病急、变化快、病情重,在短时间内可能出现危机生命的并发症,甚至死亡。心内科可以说是临床各个科室中风险和压力最大的科室。陈红牢记医者的使命,坚守医者的职责,不断攀登心血管疑难和重症疾病的诊治高峰,同时以临床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的基础、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在中国人群的调脂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急性冠脉综合征早期预警和规范化救治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率先在国内开展了他汀联合贝特类药物等多种适合中国人群的调脂方案研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血管内皮功能损害为主要表现的他汀类药物的“撤药综合征”;积极探索并发现数个有重要临床转化价值的急性心肌梗死早期预警新型生物标志物;开展急性心肌梗死早期救治的T3转化阶段研究。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等课题,先后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中华预防医学科技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华夏医学科技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等。
33年的从医生涯中,陈红教授长期奋战在临床一线,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挽救过数不清的生命,为许多心血管病患者赢得了重生的机会。“陈大夫,你的服务态度真好,每次来都看到你笑呵呵的,听你分析完我就放心了,感觉病都好了一半。”这是很多患者对陈红教授说过的话,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需要每天面对患者被心脏疾病折磨的痛苦面孔,反复的焦虑、呻吟与抱怨,也许职业的特殊性,会使大家淡漠了同情心。但是,陈红教授时刻牢记职业赋予的使命,始终把病人放在与自己的同等位置上,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一直以“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设想去指导自己的言行,不论职位高低,不管贫富贵贱,尊重每位患者的人格,每天以真诚的微笑减轻病人的思想顾虑,以亲切的问候拉近与病人的距离,以完美的解答让病人轻松的回家。不仅尽力解决患者疾病的痛苦,同时关注病人的心理需求,深受患者的喜爱及家属的信任,以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为老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在学生心目中,陈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慈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她总是从严要求,倡导并身体力行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学风。生活上,陈老师是如慈母一般的长辈,她几乎记得每一位学生的生日,经常为学生们买来惊喜的生日蛋糕。逢年过节时,有因为值班回不了家的同学,陈老师总会亲自请学生们到自己家里吃团圆饭,感受家庭的温暖。小小的故事,包含着她的细心,承载着学生们的感动。
陈红教授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医生与匠人的区别就在于,她是在与生命对话,她需要感情,需要富有爱心和洞察力。患者的病痛需要医者感同身受,他们选择你就是信任你、依赖你,我们用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赢得患者的身体健康,这份成就感和幸福是其他职业难以给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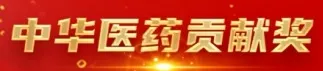
中医科 王少杰

王少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中医药传承指导老师,北京市第四批名老中医专家,首都名中医,北京市“双百工程”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主持并参与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重点行业专项科研项目、多项首都科技联合攻关项目;兼任北京中医药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肾病委员会委员。
王少杰:以静稳病人焦虑 以柔传仁爱之心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袭卷京城,大量患者涌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那时人们对SARS病毒认识不全面,且物资匮乏,缺少隔离衣、护目镜等防护设备,医护人员只有纱布做的薄口罩,每天要用肥皂洗洗晾干后再次使用。为了切断传染源,4月24日医院被封闭,来上班的王少杰被隔在医院大门外,此时她想到医院只有中医科可以煎药,院内还有医生、护士需要用中药治疗,王少杰没有回家,她说服了门口警员,进到中医科煎药室,并一个人担负起了全院24小时煎药和送药工作。
为减少感染,王少杰一人要为二三十位隔离在院的感染医护人员诊疗。没有防护服,就把诊桌放在窗户边通风看病;没有防病毒口罩,就用开水烫过的纱布垫在口罩内,每日更换。“我不能倒下!如果倒下,被隔离在院内的医患人员就吃不到中药了”,她想。直到医院解封时王少杰才知道,生病的父母在一个月内去世了,她都没能见父母最后一面。
王少杰的努力,让喝中药的患者7天退烧且没有后遗症。医院解封后上报抗击SARS先进工作者时,她报了中医科其他同志,唯独没有上报她自己。
王少杰是中华肾病学会的专家会员,几十年用纯中药为治疗肾病积累下了经验。2010年的一天,年仅26岁就双目失明的赵玉被扶进诊室,她进门边哭边诉说:“不要抢救我,我的肾病了,眼睛瞎了,看不到我刚刚生的双胞胎女儿,瞎眼活着痛苦,还不如不救我。”患者赵玉被诊断为:孕32周HELLP综合征,双眼视网膜脱落(渗出性),尿蛋白,心包积液。多日抢救后,赵玉生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可双眼失明、肾功能不全让她痛不欲生。经过中医治疗,她的肾功能回到了生产前的健康状态,视力也完全恢复……像赵玉这样的患者痊愈后,都会把宝宝的相片留给王少杰作纪念,这样的相片放满了一整本相册,有的宝宝现在已经上了大学,还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了。
王少杰的诊室四面墙上,挂满了全国各地患者送来的锦旗,她的患者中,很多是在数个医院治疗后又到她这里,还有不少是经过治愈者口口相传而来就诊的危重病人。门诊中的王少杰,总是微笑着面对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人,都能让他们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解过来,再通过细致耐心的问诊和安慰,提高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作为中医科老主任,王少杰深知“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争艳才能春满园”。她把每次获奖的奖金全部捐出,带领全科走红路、学英烈,其“初心不改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人。不仅如此,她还赴河南实地学习张仲景的中医专业理论,为更好地提高中医专业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王少杰克服种种困难,亲自设计中医科门诊就诊环境,让病人在古香古色的环境中候诊,这种环境起到了静心态、安神明的作用,有助于患者们提高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在综合医院里,把中医科建成有病房、有门诊、有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实验室,并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博士生、中医师承学生,王少杰对中医药的实践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风湿免疫科 何菁

何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委员;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荣获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
何菁:敢于质疑 勇于攻坚
2009年,作为主治医师的何菁已在病房轮转1年,面临各种治疗,她内心积攒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书本、指南和文献似乎不能解决很多棘手的救治问题。按照经验,遇到瓶颈时,她通常会先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从机理上归纳出失败的原因。这次也是如此。
一篇发表于2008年关于T细胞亚群,特别是滤泡辅助性T细胞异常直接辅助B细胞分化的论文吸引了她,由此,何菁开始了探索之路。每天中午,她会从检验科取走自己患者化验剩余的临床标本,边吃饭边离心、染色、固定,晚上下班后上机,坚持进行了2年多相关的流式免疫细胞学研究,终于在2012年首次在自身免疫病中发现了新的免疫细胞亚群——pTfh细胞,并揭示了其在自身免疫病中的致病机制。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专利,并获批北京市2018年新增医疗检测项目,在临床常规开展,用于患者病情监测和指导用药,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各科室的临床大夫们也经常来讨论这些免疫细胞在其他疾病中的应用。例如,血液科大夫根据它来调整GVHD患者的治疗;生殖科大夫称,不良妊娠患者很受益;皮肤科大夫则表示,患者治疗效果很好……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何菁看得越多,就越质疑现有的治疗方法。她通过细胞亚群检测发现,很多重症患者淋巴细胞,包括Treg细胞已经很低了,但临床还在按照指南进行激素冲击和大量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导致患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何菁敏锐地意识到不对,于是,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她第一次开始使用低剂量白介素-2(IL-2)治疗红斑狼疮,随后又开展了多项临床试验,在科室主任和团队的支持下,发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白介素-2的通路缺陷,并成功用低剂量白介素-2靶向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此前,这一疾病无特异性治疗,常用药物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毒副反应大。低剂量白介素-2作为受体靶向生物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新疗法,不仅显著提高了疾病缓解率,还不增加感染等毒副反应,解决了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导致感染和致死的临床难题,使大量患者受益。该成果为我国制定首个《低剂量IL-2治疗SLE的推荐意见》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白介素-2的临床应用研究,被同行高度评价。
在学术领域,何菁经常受邀参加国际大会并发言,推广我国先进的诊治进展,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推动了风湿免疫临床医疗的发展。作为临床型导师,她深知对待患者和对待科研是同样的,信心和耐心非常重要,科研之路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途径,只有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才会有点滴收获。因此,她带领团队在奋进中坚持,并且不断树立信心。在研究教学方面,何菁虚心听取学生和下级大夫的意见和建议,既能静下心来埋头苦干,也能大胆放弃、敢于创新和挑战权威。
“无私奉献,言传身教,做青年同志的引路人。”这句话是何菁的真实写照。20多年来,她从一名医学毕业生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学术骨干,在风湿病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怀着对医疗工作的满腔热情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地耕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一名正能量传播者,为广大青年医师树立了榜样。

眼科 王凯

王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眼视光学会副会长,北京医师协会眼视光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医促会视觉健康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眼视光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节目嘉宾主持,长期从事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近视眼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王凯:青少年近视防控之路的求索者
作为一名眼视光医生,王凯每次出诊都会被家长和孩子围得水泄不通,“近视”不光是孩子看不清楚那么简单,背后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牵盼。
王凯曾在门诊中遇到过一位5岁患者,孩子双眼近视达300度,询问病史发现父母视力都很健康,并无家族遗传倾向。但王凯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孩子哭闹时,姥姥都会把iPad作为“哄娃神器”,久而久之孩子产生了依赖。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因此王凯要做的不只是为近视青少年患者开出方案,还要向家长们普及近视防控知识。
低龄儿童近视后,度数增速非常快,如果不采取正确的近视防控措施,往往孩子小学还没毕业就会发展为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与很多致盲性眼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等密切相关,因此近视防控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针对低龄儿童的近视现状,延缓近视发展是重点。每当王凯提议帮孩子配离焦框架眼镜时,家长大多会心存疑虑:这么小就让他戴眼镜,可不可以再观察半年?虽然王凯可以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医学更需要客观冷静。他会耐心和家长说明,孩子已经是真性近视,就算观察再久,也不太可能重回不近视的状态,不戴眼镜只会让近视度数涨得更快。但一些家长还是有执念,不愿给孩子配眼镜。
深耕科普领域多年,王凯除了在中小学举行科普讲座,他还在新冠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媒体平台,为大众传播护眼知识,获得了家长和学生们的好评。
王凯表示,没有哪个孩子会无缘无故的近视,更不会突然涨成高度近视,如果家长能提早了解近距离用眼及电子产品对视力的危害,从三岁开始就给孩子建立屈光档案,掌握正确的护眼知识,门诊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低龄近视儿童了。这也正是王凯数年如一日坚持做青少年近视科普的强大动力。
在给孩子看诊问询时,更多的是王凯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他一方面能感同身受家长那种既慌张又茫然的情绪,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具体可行的治疗方案给予家长安慰。
王凯一再表示,近视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近视发生后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凭其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甚至引起一系列致盲性眼病。面对成人近视,特别是想通过手术方式摘镜的患者,王凯会着重强调“手术可以摘镜,但无法彻底根除近视”的理念,比手术更有效的方式,是建立科学的用眼习惯,少看电子产品,增加户外运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人们感触世界的通道,视力健康与否直接与生活的幸福指数挂钩。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是社会公共卫生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共建。漫漫行医路,身为一名眼视光医生,王凯的目标是成为青少年近视防控之路的求索者,以平凡之力守护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