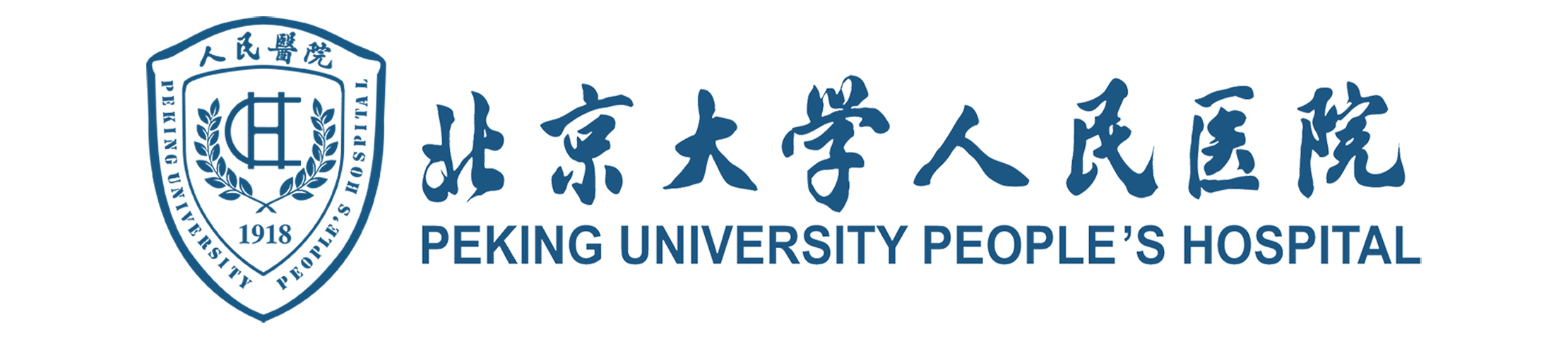《北京日报》:胡大一的加减法
关于胡大一,网络和纸媒对他的介绍很多:中国心血管界的顶级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北京军地多家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中心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主任委员、“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获奖者……
看胡大一看病,既简洁明快又趣味盎然,无枯燥刻板之感。我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多次见他给患者看病。例如2006年7月26日,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我事先从胡的助手处得知消息,没有惊动他本人,悄悄来,躲在人群中观察。这是上午,有六七位胡的学生在场,他共看了16位病人。我依次做记录如下:
一、现役军官,大校。胡大一:你这个病,好比人到了岁数,长出几根白头发。没关系,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不要轻易冒风险,付不必要的代价。大校:听胡主任说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言罢又询问倍他乐克性能,胡大一随即道出该药四大用途。
二、男,63岁,几家医院对其病症各有判断,莫衷一是,特来请胡定夺。该患者啰嗦,叙述冗长,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车轱辘话来回绕。胡不厌其烦,耐心解答。
三、女,36岁,自感心虚、没劲,海淀某医院说她心肌缺血,冠心病,建议做冠状动脉造影,费用五千元。胡: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你得冠心病的可能性是零,百分之一都没有。你的病吃点谷维素就管用。
四、女,年龄不详。胡:不用作检查,无器质性问题,神经调节就可以了。不要花钱买紧张,没得心脏病,倒得了心病。
五、男,年龄不详,南方口音,短裤,秃头,小伙儿模样。胡:放心吧,没大事。
六、男,年龄不详,胡建议门诊检查,不必住院检查。
七、男,78岁。胡:咱们的心脏比较老了,是用过多年的旧机器。正常的退行性变化,别怕。
八、男,51岁,开车族,常食荤腥,不锻炼。胡不主张多方寻医,建议走步,说自己就走,边说边从腰间取下计步器展示说,今天我已走了九千步,还差一千。
九、漏记,笔记本上记的是一首早年军事歌曲的歌词:“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一支美国枪……”盖因当时,笔者脑中奇异地响起这首老歌的旋律,觉得胡大一面对冲上来的种种问题,真是从容不迫,应对自如。胡大一撂倒和俘虏的是什么?缴获的又是什么?
十、男,69岁,“地中海”发型。胡审视他带来的一沓单子,连声说,这个药不用开,这个T波变化没事……
十一、男,45岁,主诉焦虑、惊恐、怕坐飞机。胡:别担心,跟心脏无关,是心情,太紧张了,生活方式要改一改。建议多走步,快走,一分钟走一百步才有效果。
十二、女,50岁,心脏做过支架介入手术。胡建议不要减药。
十三、男,55岁,外地人,胖子,爱吃肉。胡:还是要严格控制饮食。陪同就诊的儿子在一旁抱怨:上次胡大夫都说了,你就是不听。
十四、某人,性别漏记,给67岁的父亲打听病情。胡看完病历,正色道:已经很严重了,应尽快入院。听说患者现住辽宁鞍山,胡当即请子女开通手机,亲自跟患者通话。收线后建议,不要来京,立刻入当地医院治疗。
十五、女,54岁。脸色木然,总感到饥饿,心率偏慢,每分钟44次。医保关系在人民医院,在那边不容易挂胡的号,特意赶到这里。
十六、小孩,会诊性质。
我的笔记本上,还记有其它一些信息:
整个上午,胡大一未离开诊室,只接一次单位电话,喝一口水,没上卫生间。
中高身材,精力充沛,眼睛明亮,近视特有的老花眼:摘下眼镜看病例。
用普通血压计。戴听诊器。
把脉,宁静沉稳,像老中医。
测心,左手平放患者胸前,右手指轻击左手。
诊疗方式省钱、费事,需要功力,需要认真接收病人各类信息(言语、表情、病历、身体状况等等)。
敢下断言,形象,有说服力。卷平舌不很分明,有口音,管“老百姓”叫“老白姓”。爱做健康宣传,总是建议病人吃饭要吃八分饱,每天运动一万步,少吃肉,不吸烟。爱说:随时来找我。并不是随便一说,而是给患者电话号码。
当天,除了记录,我私下还有一次提问。尽管我没打招呼,但胡大一应该发现我的到来,有我这样一个拿着笔记本的观察者在场,他可能会格外认真,遂向身边一位学员试探说:今天的病人有福气。
学员不假思索:哪天都这样。
胡大一的看病过程,有一个“内核儿”值得一说,姑且叫做:胡大一的“减法”。“减法”应是医生题内应有之义,减去病症,减去疑虑,减去负担,无病无痛一身轻。
现在,许多大夫看病爱叠床架屋,滥用手段。你报了病名,他并不多问,甚至不愿多看你一眼,而是马上埋头,唰唰开单子,让你查查这个,验验那个。
与此相反,胡大一看病时爱用“减法”,减去一项,再减去一项。
某些医生的滥用手段,不一定是医术不过关,而常常是利益驱动。
过度治疗在心血管领域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滥用支架。胡大一对滥放支架牟取暴利等过度治疗行为,一贯持否定态度,多次予以强烈谴责。2012年秋天,他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以及自己的微博上,仍然强调:我国存在稳定性心脏病患者心脏支架放得太多的情况,而且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有些患者一次放入3个以上支架,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几个。其实,很少人需要置入3个以上的支架。
胡大一认为,过度治疗的原因,一方面有医生的医疗水平、道德水平问题,医生待遇过低、院方管理过松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患者的认识问题。患者来看病,就是希望看出病来,说得悬乎点,可以让大夫重视。总之双方都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
说有病容易,说没病难。西医的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说:“不要做得过多。”中国古代圣贤也说:“过犹不及”。胡大一凭借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为病人负责的精神,敢于给一个个被“判刑”的病人“减刑”或宣告“无罪”。
但是,胡大一的医疗思想和行为,又很难单纯用“减法”来概括。因为很多时候,他采用的不只“减法”,还有“加法”。 “加法”也是医生,尤其是现代医生题内应有之义——给病人增加信心和勇气、温暖、抵抗力,给医疗事业加上宽广视野和系统精神。
胡大一反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僵硬模式和“坐堂医生”枯等病人的老旧套路,主张从健康和疗效出发,走出去,到更广大的空间行使医生职责。他有两个做法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从1980年代开始,他就结合具体治疗,随时随地向病人做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并在各地开设公益讲座。这种讲座,常常给组织者造成麻烦,因为组织者总是对听众对胡大一的欢迎程度估计不足,不是场地安排小了,就是时间短了,最后只得不断顺应踊跃而来的听众要求,把场地换大再换大,把课程延长再延长。胡大一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和深厚学养,把科学健身防病知识生动地送到人们心中。口头普及之外,更有笔头功夫。他在撰写科研论文的同时,不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写作科普读物。他的《高血压居家调养自疗金典》《冠心病居家调养自疗金典》《降血压降血脂药怎么吃》《国人健康手机号-14065430268》《咖啡无罪的101个理由》等出版以后,深受读者喜爱。
二是开展“爱心工程”。他发起并组成一支志愿者医疗队,利用节假日和周末,到全国各贫困地区,为农村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义诊。从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胡大一爱心工程专家志愿团队在全国各贫困地区开展大型爱心义诊和健康讲座200余次,筛查近40万人次,指导和开展手术6000余例,资助爱心基金和器材近3000万元。10年来,他们和20个省市75家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为贫困地区患者诊治时,全免专家挂号费,只需交彩超等各项检查费80元。治疗费(器材、手术、药物、住院等费用总和)控制在2万元以内,如当地平均标准低于此标准,还会有进一步的优惠举措。
我参加过一次爱心工程活动。那是在河南台前,寒冷的朔风中,我见到当地农民、患儿家属、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爱心工程发自内心的欢迎。在去台前的火车上,我跟胡大一有过一次特殊的交谈。时逢胡教授身体不适,嗓子发炎,说不出话,只能伴着列车的震响,从喉管发出嘶嘶的声音。我说你休息吧,咱改日再谈。他不干,摊开本子笔谈,一字字,一行行,密密麻麻,写出他对中国医疗现状和爱心工程的种种见解。印象里,中国的许多医生都不愿好好写字,不知是出自职业尊严呢,还是怕外人瞧出门道。胡大一的字写得很清楚,用词也准,方方正正,明白晓畅。不论是跟我笔谈,还是办讲座,写板书,写处方笺,大家都看得懂。
胡大一有一句名言:“对待病人,视年长者为我父母;视同年者为我兄弟姐妹;视年轻者为我儿女;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该给病人做的检查一项不能漏,不该给病人做的检查、开的药一律不做、不开。医生的天职是看病,不是卖药,不是收红包。”
胡大一的“加法”和“减法”,跟他的大医疗、大卫生、大保健概念密不可分。当下中国的医疗领域,常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庞大的楼宇,里边横平竖直,分出了无数小格子,比中药匣子分得还细。这个楼宇重局部不重整体,重分工不重合作,重病理不重心理,重治疗不重预防;重当下不重预后,依赖机器;过度治疗;“有罪判定”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完整的病人进了大楼,很快就被“分割”开来。医生眼中的病人似乎不是囫囵的身心,而仿佛是一坨坨单摆浮搁的肉块。
胡大一认为,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价值体系也出现了混乱。疾病只是病人的一部分,医生绝不能见病不见人。要走出传统落后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理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社会-生物-心理”的全新医学理念,给人们带来完美全面的身心健康。
胡大一的“加法”和“减法”,还跟他的身世密不可分。
胡大一生于开封的一个医学世家,自小兴趣广泛,文体兼长。他说:“我是这样一个人:在中东部长大,对西部有情结;在平原长大,对高原有情结;在大城市长大,对农村有情结。”
中学时他就下乡支农。北京医学院大学6年,更是跟农村和边远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时城里斗斗斗、批批批,胡大一却参加巡回医疗队,到河北宽城一带,为农民治病。宽城地处偏远山区。早年风行一时的电影《青松岭》中著名的反派人物钱广,据胡大一说,其原型就出在宽城。去宽城,先从北京背上行李,步行拉练到承德,再转乘汽车到平泉,几经周折,卡车、马车、“11号”,多种方式并举,方能抵达目的地宽城。
巡回医疗队的带队老师,是多年后以敢说真话赢得世人尊敬的钟南山院士。房东二石,聋哑人,满身虱子。胡大一在二石家吃“派饭”(被村镇当局分派到社员亦即村民家吃饭并交钱粮票),跟二石住同一个屋,用同一根扁担挑水、挑粪。当时的媒体和文件管这个叫“三同”、“三关”: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在宽城,胡大一这个学西医的年轻人,学了不少中医药知识。山水林木之间,他学会辨识、采集100多种中草药。踏碾船,捣铜钵,生柴火,向当地老药工和赤脚医生学习制作丸散膏丹。白天忙了一天,夜里经常被喊醒,翻山越岭,处理紧急病症,比如胆道蛔虫引起的剧痛,婆媳吵架喝农药自杀,中毒性痢疾,哮喘,大叶肺炎,等等。说来耐人寻味,方圆百十里,整个县,整个地区,竟没有一人得冠心病,得糖尿病,心梗更是闻所未闻。当时,胡大一压根儿想不到,将来有一天,自己会成为闻名遐迩的心血管专家。
1970年10月,经过河北茶淀卫生系统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后,24岁的胡大一被分配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
纸上关系留在城里,肉体和精神,多数时间仍在乡间。1971年至1973年,胡大一到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带教医士班,巡回医疗。胡大一去的地方,从名字——冯家屿公社榆树底下大队喇叭茬子生产队,就能感受到它的偏远荒疏。“穷啊,真正是一家就一件衣服,换着穿,谁出门谁穿。”大人小孩也算有眼福:见过飞机——北京到东北的航线正好在这一块天上经过;也算没眼福,从未见过火车、汽车。没钱,修不起路,别说汽车,小型手扶拖拉机都开不进去。
1974年至1975年,胡大一的命运有了新变化,走得更远——河西走廊、甘肃酒泉一带,所见更穷、更荒凉。一行人兴冲冲赶到兰州,脱下百姓衣衫,换上草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不算军人,算是北京医疗队,总理周恩来派来的,名义:为西北人民送医送药。天苍苍野茫茫,可是,风吹草低却没见牛羊,倒是突然冒出了许多猴子,挤挤擦擦,装了一车又一车。胡大一有些纳闷,猴子它应该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啊,到这儿来是怎么回事?胡大一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所在,并不简单,是氢弹试验的外围地区。
当地极度缺水,卫生条件很差,区区一汪浊水,人畜共饮。奉上级指示,他们既要当医疗队,又要当宣传队。胡大一拜幼年爱好所赐,为老乡吱吱嘎嘎拉二胡,一位血液科老教授会拉京胡,他们扯着喉咙唱样板戏,《海港》《龙江颂》《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哪里有湖?哪里有港和江?只有一片戈壁滩,飞沙走石、寸草不生。胡大一风尘仆仆,在当地查水,查癌细胞,查各项规定下来的指标,衣领和鞋壳里全是土。事隔多年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为核试验服务去了。
1977年,胡大一的足迹向着愈发边远的荒漠地区行进。所到之处,不但贫困,更充满大自然设置的种种危难险阻。那是在著名的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服务对象主要是藏族牧民和当地的边防部队。“生存环境特别残酷,在阿里,每人每月发几箱红蜡烛,特大号的,每根都有锹把粗,在北京从未见过。整个医院只有一台小发电机,隔三差五,经常停电。没有机场,无法通信,半导体广播也不灵。”
雪域高原,零下40几摄氏度的低温,没有取暖设备,晚上把柳树根子烧红,趁着有点儿热乎劲儿,赶紧睡。那也不容易睡,满屋子烟气,呛鼻子,熏眼睛,鼻子蒙住,眼睛闭上,照样熏。胸中迷雾多缭绕,泪眼模糊入梦来。还有雪崩。
工作时缺氧,休息时照样缺氧,胡大一周身乏力,脑瓜仁儿隐隐作痛。别人打扑克,说大脑不能过度使用,需要静养。胡大一的静养方式是躲在一旁,摊开影印的英文版《希氏内科学》,抄卡片,查字典,坚持把这厚厚的一大本教材啃下来。其它医学书籍乃至油印讲义,找到一册研读一册。稀薄的空气中,锹把粗的蜡烛不知能点出什么样的火花,但只要是火花,总能照亮青年胡大一、雪原胡大一的身心。
1979年,胡大一回京做临床大夫。工作之余,他投入精力最大的,是学英文。年近40的胡大一异常刻苦,一丝不苟地练听力,练读写,还抓住一切机会练口语,遇到外国人来访,上去就对话。同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胡大一想当“间谍”,仿佛中国的心血管领域有什么重大机密值得向境外情报机构透露。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作访问学者,研修方向:心脏电生理和介入心脏病学。学习期满,胡大一脑子里、行囊里携带着磅秤和货币无法估量的宝贵信息和资料,动身回国,一天没耽误。“有人说我不会回来,我还真就回来了。我不是为了堵他们的嘴。用不着。我是真想拿着学到的东西,回来干事。”
1991年10月4日,对中国心血管医学领域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胡大一在国内率先开展射频消融导管新技术,治疗快速心律失常,为中国在介入心脏病学方面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走出第一步。胡大一被公认为“中国射频第一人”。此后几年,胡大一在上百家医院及东南亚数国推广普及这项技术。他多次带队赴印度和越南讲学、做手术,被印度专家称为“射频大使”。
描述胡大一的经历和性格特点,似乎可以不断借用他名字中的那个“一”。什么事,不干则已,一经决定,就一头扎进去,一门心思,一往无前,一步一个脚印,一诺千金,一干到底。靠了这些“一”,靠了独特的加减法,胡大一在中国心血管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
大一大医。大医者,并非指的是大医院的医生、大派头的医生、大忽悠的医生,而是另有一番特定的含义。这含义,庄重,深邃,严格,古老。
1400多年以前的隋唐时期,中国出了一位医药学家,他的自然寿命很长,活了102岁,他的精神寿命更长,一直活到现在。他医术高超,两朝三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邀他入朝做官。他的德行和志向更高,一一谢绝这些“皇恩”,深入民间,深入远山荒野,采药行医,救苦救难,为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留下了永无损毁的珍贵财富。
他叫孙思邈。他在传世之作《大医精诚》中写道: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不知胡大一听没听说孙思邈的这一金石铿锵之音。但我觉得,胡大一正在继承发扬先贤的传统,为了他的“老白姓”,努力去做一名大胸怀、大抱负的苍生大医。